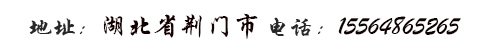我写植物记猪娘草
|
一天,在乡村农家乐餐馆里吃到一盘野菜,滑溜溜的,微微有点酸。 知晓的同事说这是猪娘苋,折断它的茎,会有白白的奶水出来。另一同事说,电视里的养生节目上介绍过,学名叫马齿苋。哦,这个我也认识,我们叫猪娘草,小时候割来给猪吃的。同事笑着说,以前猪吃的东西现在都给人吃,人吃的东西给猪吃。哈,好象说得不错。如今的养猪场,还有多少靠割草来喂养的?都是从市场上买回一车一车的精饲料,由大豆啊玉米啊磨成粉未,拌进添加剂,混合而成。 吃了猪娘草后,发现行经之处都能见到猪娘草。花坛里,草丛堆,水泥地的缝隙里,摊手摊脚地躺在那里,没人去理张它。大太阳下,一点遮盖都没有,既晒不黑也晒不死,特别是长在绿化带里的猪娘草,真是肥厚啊。在今年夏天这个 的旱季里,我家北窗台上有好几盆温室的花草,被我放养在外忘记了浇灌,都晒成了柴,点个火就能燃。比什么“荒野生存”“极限挑战”的所谓真人秀要真实残酷得多,真的是没得救。 马齿苋 既然入了我的眼,我自然要给它们拍照留念。只是它们不怕太阳我怕,难得今天下了一场雨,下班路上就蹲在路边拍。凑近了去拍,想拍得好看一些,发现有点不对头。这不是我记忆中的猪娘草啊。叶片没有那么厚,茎也没那么粗,扯断了看,居然没有奶白的浆汁。看来看花眼了。 没有奶白浆汁的马齿苋 经过体育场,看见久旱逢甘霖的紫薇,顺便也拍了几张。紫薇开了半夏,已过了繁盛期,花掉落在草坪上,掉落在水泥浇铸的边沿外,掉落在猪娘草上。对,我看见了小时候的猪娘草,单薄而细弱的身子。接着再扯呗,果然有白色浆汁。手指粘乎乎的,跟小时候一样的手感。 “行色”(识别花草的app)加“度娘”一起上,终于知道了我吃到的那个就是马齿苋,但马齿苋 不是猪娘草,猪娘草 众的名称就是地锦草。两者粗粗一看差不多,就像蜻蜓跟豆娘容易混淆。度娘说,地锦草掐断茎会有白色乳汁,马齿苋没有。另外,马齿苋茎和叶更加肉质粗壮,地锦草稍纤弱。说得很清楚,且地锦草的别名有铁线马齿苋,奶浆草……真是的宗亲啊。 傍晚拍的照片,不太清楚,茎上有白色的浆汁 “我吃草叶和花,这样我就能属于草叶和花,因为它们知道如何生活而我不知道。我叫着它们的名字和它们说话:“奶浆草”意思是叶子锯齿状而草茎带有白色奶浆的植物。但是这种草对我说的“奶浆草”这个名字毫无反应。我就试试不用“奶浆”或“草”而用其他随便想到的名字:“锯齿苋”、“针针叶”等等。用这些假名字,其实我叛变了真实的植物,揭示了这种植物和我之间的巨大空白。失态丢脸的是我其实大声对自己说话,而不是对植物说话。但是失态丢脸对我其实又是好事。我看护着牛群,而词语的声音看护着我。” “在我看来,物体不认识它们自己的制作材料,姿态手势不认识自己的感觉,词语不认识把它们说出来的嘴巴。但是为了确认我们的存在,我们需要物体,我们需要姿态手势,我们需要词语。归根结底,我们能用的词语越多,我们就越发自由。”(赫塔·米勒《你带手绢了吗》) 《国王鞠躬,国王杀人》赫塔·米勒 要是在没搞清马齿苋和猪娘草之前,看见赫塔·米勒写的奶浆草,我一定会脱口而出,这不就是马齿苋也就是猪娘草吗。叶子锯齿状,跟马齿苋这个称呼多少相称。我喂过猪看过牛,就是没有看护过马,那种适宜在北方生长和奔驰的高大物种,在江南只能作为稀奇景观才能偶尔一见。马齿苋自然无法给我一个具象反应。猪娘草,猪娘苋,奶奶草……我以为,我和同事都认出了自己眼里的植物,认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生活和记忆。可惜还是差强人意。 网上的地锦草图片,就是我记忆中的模样 也许是小题大作,不就是两种野草吗。至于搞得那么清楚,又不做学术研究。借用赫塔·米勒的话,给猪娘草正名,只是为了消灭我们和植物之间的巨大空白,跟它拉关系。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,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也许真的还抵不上你跟一株花草的亲密。 赞赏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dijincaoa.com/dmccd/408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中药分类性味功效表格总结
- 下一篇文章: 药通之声这些品种,近期市场如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