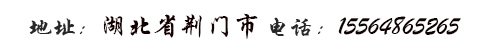浩尔沁草原
|
浩尔沁,是大浩德原来的名字,蒙古语,友好合作之意。在大浩德,七八十岁的老人,还知道浩尔沁这个名字,中年人知道者寥寥,年轻人没有人知道了。 浩尔沁草原位于大浩德与新站镇之间,14万亩,一览无余。浩尔沁草原不仅养育了大浩德的牛、马、羊,也养育了大浩德的人。 牲口是农村人的半个家,一年四季,浩尔沁草原上都荡漾着牲口,牛,马,羊,各踞一地,互不侵犯,牲口在草原上荡漾着吃草,像草原上浮动着的一朵朵花。 放牧的汉子,悠闲地抱着鞭子,在草原上打盹儿。草肥,也鲜有狼,放牧也心安,睡上半个小时,羊和牛仍能目之所及;好马不吃回头草,一直向前吃草的马,也走不远,骑上马,跑个三五分钟,也就撵上了马群。 浩尔沁草原的草,与众不同,硬而韧,不像其他草原上的草柔软,像极了这里蒙古人的性格。盛夏过后,九月初,村里会根据每户人口,把草原分下去,每到草原分派过的日子,男人们就开始抡着钐刀,卷起裤管打草了。 男人打草的姿势很是雄健,站在草原上,两脚分开一尺多远,双手抡起钐刀,以身子为圆心,以钐刀长为半径,画半圆,一挥一抡间,一片草消然落地。 打好的草,堆成垛,经过数日晾晒,拉到不远处的新站卖,就能获得一笔不小收入了。 九月间,粮食还没收割,农村没有来钱道儿,卖草的钱,就显得雪中送炭了,家里供着学生的、老人要吃汤药的、妇女生孩子,都指着这笔钱呢。 冬天的浩尔沁草原,也不白给,供养着村人做饭的烧柴。柴火多来自草原,一个筢子上挂上一个类似于巨型撮子似的帘子,就是一副搂柴火的工具,大筢的齿,撂在草原上,将干枯的草搂起,筢子满了,翻过来,往后一拉,柴火就顺着筢齿,进入帘子,帘子满了,倒出来堆成堆,一天下来,浩尔沁的草原,能给一个壮劳力半车柴火。 浩尔沁草原上有一种植物,黑绿的长椭圆叶子,半尺来高,茎旁边长着不对称的分枝,分枝上的每片叶子,都有一个黑色的点,大浩德人管它叫酸不浆。浩尔沁草原上的酸不浆,是孩子们夏日的美食,一口吃下去,酸得直咧嘴,却吃得乐此不疲。现在想来,酸不浆于大浩德的人,不正如鲁迅百草园中的覆盆子么?只不过一个是后花园,一个是大草原。 有关酸不浆的一个片断,一直留存在我的心里,小学六年级的时候,老师领着我们写一篇关于草原的文章,班主任张老师领着全班同学来到草原上,班级里岁数最小、学习好、很活泼的一个女生,扯过几片酸不浆,调皮地往老师的身上扔,酸不浆因为页面背部的黏性,就粘在了老师的后背上。 老师有前面走,身后有学生在笑,老师的脸上也漾出孩子般的笑。那个时候就想,一向严厉的老师,高高在上的老师,身上有着光环的老师,会和孩子们一起笑呃。 那天,有风,草拂着脚面,草原在脚下延长,一群十多岁的孩子,因为一片酸不浆而发出的铃铛般的笑,草原一定也记住了。 浩尔沁草原浑然天成,如果一定要分成区域,那一定以“一棵树”为参照物。 14万亩的浩尔沁草原上,只生长着一棵树。大浩德人也风趣,就叫它一棵树。 “你家羊在一棵树那儿吃草呢!别忘了一会儿赶回来。” “你爸赶着马车过了一棵树了,快去迎一下吧。” 村 这样说话,一棵树成了一个地标。 一棵树在浩尔沁草原快一百岁了,它顽强地站在那儿,像一个统帅,草原上一切,仿佛都是它的臣子,它见证了草原的朝雾暮霭,世事沧桑,丰草瘦水,万物生灵的秩序、本分与规则。 鲍尔吉·原野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,鹿跑得那么快,却不踩一朵花。细思,这是鹿的本分。 马驹子生下来了,就能摇摇晃晃地站起来,五六分钟后就能行走,吃上一年奶后,儿马就把它从母马身边踢开,去独自生活。这是秩序。 马吃了春天的草,长水膘,有肉没劲;吃了秋天的草,才长油膘。这是规则。 上好的马,骨细,耳小,鬃少,尾短,蹄小。这是草原上的人的经验 。 一个草原,给了植物,牲口,人,多少给养?只有你生于斯,才会领略。 感谢浩尔沁草原,感谢大浩德,让我在十六岁之前的时光里,目之所及都是草。 张青梅好人啊
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dijincaoa.com/dmccd/9336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中药的命名杂谈
- 下一篇文章: 60项类产业,将享受国家重点关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