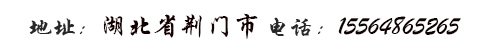故事爱上公主的准驸马,我仗着占卜女官身份
|
作为占卜女官,一向老实的我却撒谎了,我谎称公主和她的准驸马八字相克,不宜婚配 因为我喜欢这位准驸马,喜欢到肝疼 所以他只能是我的 1 一向老实巴交的我说谎了,说的还是弥天大谎。 皇太后看完我卜出的卦词,反复确认数次,才叹道:“神官,您确定九儿与于大人会八字不合,相克相冲吗?” 我装得傲然冷静如往常,矜持地颔首,淡淡地道:“正是,于修大人,并非九公主的良人,还请太后另为公主寻觅良配。” “话是如此……可他们两人如今是……” 我继续以遗世独立,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语调道:“这世间多少怨偶开始不都是蜜里调油的吗,何况于大人与公主不过相识刚满一个月,光顾眼前的虚景,又如何能看到往后的缘分,怎么,太后是不信我?” 太后连忙为自己的质疑道歉,我是神门子弟,历来被皇家所倚重,怎么会为了区区一个公主的婚配而说谎呢? 事实上,这个谎对于我来说,太有必要了。 因为我喜欢这位少理寺大卿于大人,喜欢到肝疼。 我想,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女子可以大方到,愿意做心上人的红娘,还说出“这两人乃天作之合啊”的判词。 很快,九公主的婚事定下来了,出乎大家意料,公主被指给了镇国大将*的幺子。 当时我站在帘幕后面,看到朝堂之上的青年呆愣当场,原本喜悦的俊脸因为噩耗而变得呆滞惨白,好像一向挺直的脊背都要被这晴天霹雳给压弯了。 我看着于修的样子,也跟着难过起来,但我很清楚,这时的疼痛,必然小过看到他与公主喜结连理时所要承受的苦。 2 没有人会看出蹊跷,除了一人,我的师兄,当朝国师江配灵。 当年师傅收了两位弟子。我主内,为女神官,说白了就是皇族的专属占卜师,杂七杂八莫名其妙的都得我负责;江配灵主外,为一朝国师,主测国运。公主婚事定下来的当晚,我这位师兄来到我殿中,劈头就来了一句:“施染,你不要命了吗?” 我仰头看着这位师兄,说实话,很胆战心惊。 他白袍黑发,五官俊美得有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美感,神情冷漠神秘,比天上最朦胧的月色还要美蔺。 宫中甚至有传言,说他有上古神族血统。 我还想骗他,嬉笑着说:“怎么会呢,我们算命的,不最惜命了吗?” 他从不与我废话,道:“惜命?惜命你会去破坏别人的姻缘?你应该知道,拆人姻缘刻意改变他人命数,得付出什么代价。 但到了最后,师兄都没有拆穿我。 他当然不会,我理所当然地想,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,俱荣俱损,他自然不会去黑自家招牌。 初春踏青,于修已经身形消瘦,越发显得清俊傲骨,他找我喝酒,一杯一杯地往自己肚子里灌,喝到眼神变得迷茫,再也看不出一点清明。 他呢喃着:“染染,你说这是为什么呢?” 我想,他是怎么也不会想到,那个分开他们这对牛郎织女的恶人,会是我。 也亏他醉了,听不出我的心虚,我说:“当驸马压力很大的,没什么好的!喏,瞧大公主家的驸马爷,明明也有才华,却总被人在背后说是靠女人上位,一生到死就连进史书,也摆脱不了驸马爷的名头,你……” “我愿意,其他的我都不在乎。” 听着他对公主的痴情爱语,我差点心酸得落下眼泪,我一生都在为他人的命运避衰迎吉,可我却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做,才能让面前的人,多喜欢我一点。 他醉狠了,趴在桌上朝我露出温柔而充满爱意的微笑:“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,她就蹲在御花园的牡丹花旁,好像在对花儿说话,她那么美好……” 哇!对着花儿说话,这九公主的人生也无趣到一定境界了吧! 明明没见过几面,就互相倾心,就非她莫属了,而我与他相识五年,整整五年却掀不起一丝涟漪,早知道,我也去花园里装傻对空气花朵说话了。 为什么人与人,就得差别那么大呢? 其实我以前一直以为,于修对我,并非无情。比如他会记住我无意间透露出来的喜欢,然后冒着风雨将我喜欢吃的糕点送到殿里;又比如在上次新年宫中晚宴时,我厌恶酒色艳舞,悄悄溜走时他也会跟上,拉我去湖畔边上赏月畅侃天下趣事……零零总总,数不胜数,我总是以为,他对我的好,是出于好感,但我现在明白了—— 这些所有的情谊,也许全部,只是出于我单方面的自作多情。 我再也忍不住,压抑着无所遁形的酸涩苦楚,俯身在于修光洁的额头上亲了一下。 短暂得如同蜻蜓点水一般。 身后传来树枝被鞋轻微压断的声音。 我惊慌回头,只见绿影花丛之中,有人静静地站在那里,也不知道站了多久,宽大的袖袍边上都染了雾气。 我顿时像正在做坏事被家长突然抓了个正着的孩童,手脚都不晓得往哪里摆,说什么话也都像是在为自己的错误作解释。 “师……师兄。” 他没有回应我,拂袖离去。 3 镇国大将*家迎亲那日,举城欢腾。 我并没有去喝喜酒,就躲在殿里听心腹回来汇报情况。 但我怎么也想不到,心腹给我带回来的消息是,于修因途中挡公主婚轿,试图阻止婚礼,而被关入狱中。 我一失神,手中的茶盏掉落在地,摔成碎片。 这回糟糕了。 如果只是中途拦轿这一点,于修顶多挨下批,降一下职,罚一年俸禄——只是这事伤了大将*府的面子,就危险了。 大将*权倾朝野,为人跋扈,其幺子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,是锱铢必较之人,于修与九公主的事又满朝皆知,只怕将*府不会轻饶于修。 我心系于修安危,连夜打通关系来到牢狱之中,于修背对我,面朝墙壁,似乎在沉思。 我隔着铁栏,半天才说:“你……你怎么做了这种傻事呢?” 于修转过头,脸上带伤,但眸子还是明亮的:“对不起,我那时……好像中了魔一样,完全控制不住自己,见到轿子就发疯了。” 夜间的凉气又开始渗入骨头里了,连站立都很困难,我吸吸发红的鼻子:“人总有犯傻的时候,不要紧,你安心在这里养着伤,我会把你弄出去的。” 突然之间,不祥之气扑面而来,我靠着六感微微旋身,只见一支利箭从狱中窗口里飞入,贴着我的面颊,又直直地射入了墙壁之上。 于修突然脸色大变:“小心!” 我慢慢地平复心跳,拔出那支箭,左右检查一番:“没有标志,但看这用料做工,必是将*府的手笔。” 4 今夜的京城,出乎意料的安静,静得让人有些毛骨悚然,连打更的声音都未曾听到过,只有偶尔飞过的乌鸦发出嘶哑的鸣叫。 艰苦,只是往日朝思暮想的人就在身旁,再多的辛苦也都成了甘之如饴。 只是离开京城后,我竟莫名地生了一种怪病。白日还好,一到入夜时分,特别是到子时的时候,全身疼痛难当,这并非是肤浅在表的皮肉之痛,而是深入骨髓,连灵*都为之冻结的巨痛。 开始我还能忍,但我发觉,离京城越是远,这痛便越深。 于修以为我面色差是长于宫中身体娇贵无法吃苦,他对我心有愧疚,日日欲做牛做马地照顾我,十分体贴。 但我知道,这种体贴只是一种报恩,是一个人欠了另外一个人时,方有的感激之举,并非发自肺腑,源自情爱。 “染染,你不是会占卜吗?那你算算咱们是要往哪边走?” 又一次从客栈里落荒而逃后,于修问我。 为了掩人耳目,我一直作男子打扮,也许本身彪悍气质难自弃,我装得十分得心应手,我甚至打趣说:“喂,兄弟,下次你装姑娘吧,我们就可以扮夫妻了哦。” 他脸颊微红,正色训我:“姑娘家不要说这种话,我发现了,你一出京就越发无法无天了,流氓习气不好,得改!” “啊……大家兄弟那么久,你就不要跟我计较这些了吧,至于往哪边走嘛,你不知道算命的人,是永远算不准自己的命运吗?” 故意装作没有形象,扮作毫不在乎,只有用这种办法,才能不让他察觉我对他的心意。 “如果不是我,你还是宫中神官,也不会像现在这样……” 我打断他的话,故作不在乎:“为朋友两肋插刀,我愿意——而且谁想一辈子待在宫中做井底之蛙呢?” 于修问:“那你最想去哪里?” 马车奔驰时扬起的风吹乱了我的头发,我嘴里叼着狗尾巴草,回头对于修朗然一笑:“去哪里都好,去江南也好,去大漠也行,只要能看到跟宫中不同的景色,我已满足。” 他微微愣住。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我并未说出口,再好的风景,没有你,都欠缺一分,不会圆满。 6 子夜时分的剧痛让我陷入错乱之中。 我隐隐听到耳边有缥缈的雨声,滴答滴答,我记起来了,师傅死的那天夜晚,外头也有雨。 师傅临死前没有见我,当时我与师兄跪在殿外大门处,屋檐上溅落的雨洒在了我的鼻尖上,江配灵用衣袖擦干我面上的湿气,他动作很轻,一直说没事,莫哭了。 不久之后施针的大夫出来,他说国师要见江少爷。 白日里庄严肃穆的高大殿门如今显得阴森可怖,就连缝隙间都透着一股死气沉沉,我一个人跪在门口,膝盖发麻,也不知道跪了多久,只知道最后是江配灵搀扶着我站起来的,他面色平静,只是握住我肩膀的手,不停地发抖。 “师妹,师傅已经去了。” 我瑟瑟发抖,无论他怎么轻拍我的背脊,我都控制不住地痉挛起来。 他递给我一张金箔纸,动作庄严:“这是师傅给你的命批。” 一时间,我都没有勇气打开这张纸。 神门有规矩,只有当一个人要死的时候,才能为自己的徒弟批命。 我那时已经看过无数人的命数,却一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是如何。 我一边哆嗦着一边打开了那张纸,里面字迹苍劲有力,有条不紊,的确是师傅从前的字迹。 只见里面写道:染儿,你命有劫难,只有京城宫中皇气能保你一生平安,若离开京城则会命运坎坷,必会早亡,缘分不能强求,望惜福,谨记师言。 我彷徨地问江配灵:“师傅的意思是,我一生都离不开这儿了吗?” 牢笼一样的皇宫,透不过来气的天空,难道我一辈子都得像囚鸟一样被困于此了吗? 他的手紧紧地捏住那张命批,眼有戾色,字字坚决:“不会,我会想到解决办法的。” 不可能了,师傅一辈子没算错过一件事。 他说我离不开京城,我就肯定离不开了,离开的话,就会像离了水的鱼儿,唯有死路一条可走。 如今算起来,我跟着于修离开京城,已经有半年了。 醒来的时候,于修守在我旁边,他的声音好像很远,又好像很近,我恍恍惚惚地定下神,才发现于修眼中红丝密布,神情憔悴,如寒潭深水一样的声音直直地刺进我心里。 “染染,你已经昏迷三天了。” 购买专栏解锁剩余57%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dijincaoa.com/dmcgx/11686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要命的敏感肌,到底怎么治
- 下一篇文章: 秀才为母寻药,归途遇老道砍树,老道赠与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