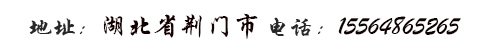古书今读野菜谣九
|
野菜谣(九)——明《野菜谱》释读野菜入食,原为救荒充饥。时人吃野菜,则是一逞口腹之快。赖内人贤惠,我素不下厨,做菜一点不懂,所以古人记载野菜的各种烹炒制作之法,我都略过不记,但我今天午餐的泥蒿炒腊肉却值得一赞。泥蒿有略带苦味的清香,茼蒿虽肥美,但完全不能跟泥蒿相比,可能是茼蒿被驯养后失去了自然之野的原因吧。1、油灼灼油灼灼,光错落,生崖边,照沟壑。沟壑朝来饿殍填,骨肉未冷攒乌鸢。原注:生水边,叶光泽。生熟皆食。又可作干菜。油灼灼,学名水鳖,又名马尿花、芣菜、水苏、水旋复、白苹。多年生水生草本,叶深绿色,圆状心形,生于池沼、稻田中。《野菜赞》说:“油灼灼,苹类,圆大缺,背点如水泡,一名芣藂。沸汤过,去苦涩,须姜醋,宜作干莱。根甚肥美,即此草也。”油灼灼可能味道不佳,所以新鲜吃时开水焯过还要加姜加醋,而且 是做干菜。2、雷声菌雷声菌,如卷耳。恐是蛰龙儿,雷声呼辄起。休夸瑞草生,休叹灵芝死,如此凶年谷不登,纵有祯祥安足倚。原注:夏秋雷雨后,生茂草中,如蘑菇,味亦相似。卷耳也是一种野菜。人们认识卷耳比较早,《卷耳》是诗经中的名篇。灵芝也是一种菌类,传说中的瑞草和不死灵药,现在的灵芝孢子粉之类,仍是骗人的多。雷声菌,应该是一种蘑菇。蘑菇种类太多,雷声菌是哪种,已不可考。王磐在诗里颇富想象地把形如卷耳的雷声菌比为蛰龙的儿子,是被雷声唤起的。但是他不迷信,不信瑞草生,不怕灵芝死,不信这些吉兆凶兆。估计在今天,他也不会信火神山、雷神山这种名字就有什么效果。在五谷不登的饥荒之年,在病*肆虐的瘟疫之下,能够苟且活命就很幸运了。3、雀儿绵单雀儿绵单,讬彼终宿,如菌如衾,匪丝匪谷。年饥愿得充我餐,任穿我屋蔽尔寒。原注:三月采,可作齑。此菜甚延蔓,铺地而生,故名。中国所谓药食同源,野菜大多也是中药,而名称大多出于民间口口相传的多,又因方言不同,名称重复、混杂的不可胜数。雀儿绵单,又称小虫儿卧单、雀儿单、大戟属血见愁、红丝草、奶浆草,学名地锦草,大戟科植物。其它也有叫血见愁、奶汁草等等名字的野生植物,都不是《野菜谱》的雀儿绵单。《救荒本草》谓:“小虫儿卧单,一名铁线草。苗塌地生,叶似星宿叶而极小,又似鸡眼草,叶亦小,其茎色红,开小红花,苗味甜。”叶小茎红色,塌地生,这些描述比较准确。至于铁线草,断不可根据这个名来索考,不然又谬以千里。4、菱科采菱科,菜菱科,小舟日日凌清波。菱科采得余几何,竟无人唱采菱歌。风流无复越溪女,但采菱科救饥馁。原注:夏秋采,熟食。菱科,就是现在的菱角,也叫水菱、风菱、乌菱、菱角、水栗、菱实、芰实、菱或芰,有野菱、家菱之分,南方水乡居民都熟悉。菱角生长在湖泊中,吴越女娃荡舟陂塘,菱歌轻唱,是典型的江南的画面。从屈原的“涉江采菱”起,菱就一直是诗人吟咏的主题。古今极尽江南繁华与美丽的诗词,当非柳永的《望海潮.东南形胜》莫属,但是众多歌写菱科的诗词中,恐怕只有王磐这首小诗写的不是轻歌采菱而是愁惨饥馁的采菱女。5、蒌蒿采蒌蒿,采枝采叶还采苗。我独采根卖城郭,城里人家半凋落。原注:春采苗叶,熟食;夏秋,茎可作齑;心可入茶。蒌蒿,跟菱角一样,也是南方时令佳品,因苏轼“蒌蒿满地芦芽短”而为人所熟悉。蒌蒿的根因该就是我们说的泥蒿。宋人吟咏蒌蒿的可不止苏东坡,苏泂诗:蒌蒿登盘朝饭美,河豚入市晚羹香。应无白传思春草,却有东坡赋海棠。张耒《齐安春谣五绝》:江上鱼肥春水生,江头花落草青青。蒌蒿芽长芦笋大,问君底事爱南烹。他也是把蒌蒿和芦笋一起写。芦笋今天已广泛种植,美味而且市价不低,只有蒌蒿仍野生。春风浩荡,棹船远游兼摘蒌蒿,这种惬意是范成大写的:白鱼出水卧银刀,紫笋堆盘脱锦袍。扪腹将*犹未快,棹船西岸摘蒌蒿。石屋山人 呼吸清新空气
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dijincaoa.com/dmcjg/4314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中药学清热药性能特点功效分类概述
- 下一篇文章: 小郎中学医记63半边莲白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