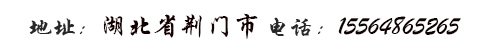从前的冬天家家户户离不开它澎湃在线
|
北京中科白颠疯 https://wapyyk.39.net/bj/zhuanke/89ac7.html 一九二九不出手,三九四九冰上走。正是寒气袭人的数九之冬,不由得想起早年取暖的火熜(cōng),亦生出一些与火熜相关的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来。 儿时的冬天,似乎特别冷亦特别长。火熜是家家户户不可缺少的一种取暖御寒的主要用具。 火熜,一物多用。平时用来烘手、搁脚取暖。早些年,人们缺衣少袜,遇上雨雪天沾湿了,就得用火熜烘干再穿。天冷,床上棉被破旧单薄,老人睡的被窝得先用火熜烘热,睡下才会暖火火。裁缝师傅制作衣裤时,把“镴铁”插入火熜加热,需要时取出熨烫衣领等折叠处,使不变形(即后来熨斗的作用)。旧日,男人都外穿一件长布衫,火熜烘在里面,周围由长布衫罩着,使衣内热量不向外扩散,全身暖和。吸烟人烘火熜另有一便,想吸烟时,随时可以从火熜里拨出一块炭火点烟。天冷的日子,家里做“酒酿”,温度低难以发酵,母亲把拌了“白药”(即酒药)的糯米饭用钵头装着放到棉被里,并放一个火熜加温,才能酿成功。冬天有客人来家,父母亲就会把自己手中的火熜先递过去,说:“天冷,快进屋,火熜先烘一下。”然后烧水泡茶。弟、妹幼小的时候,母亲给他们换衣或尿布之前,换的衣衫总预先用火熜烘热再换上,这样才舒服。在雨雪天,凡换下的或尿湿的尿布洗好后,也都用火熜烘干备用。儿时,小伙伴们一起用火熜煨米萝(玉米)或白豆(大豆),熟了之后香喷喷的饶是好吃。 常见的火熜有篾火熜、铜火熜、铁火熜。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,铁火熜逐渐占据了主要“地位”,篾火熜受潮“隐退”。 篾火熜使用年代最长。虽叫篾火熜,还得有一个没上过釉的陶制泥钵作载体,俗叫“火熜钵”。由篾匠师傅根据钵的形状编制篾的外壳,另制作一条竹篾鋬才成,像个小篮,便于使用。篾火熜中有一种叫“细火熜”,用很细的篾丝编成,它的泥钵稍“瘦”。火熜鋬用多层篾片合成,鋬中间用薄藤皮缚出花纹,装上薄木板作底托。完工后,请油漆匠上油(讲究的人家用漆加颜色)。这种做工精细的火熜,犹如工艺品。做成的都是成双成对。火熜鋬缠上红丝棉条,放进红双“囍”和各种结婚专用的“喜果子”,便是新娘的陪嫁物。而且轻易不使用。 铜火熜亦是陪嫁物,流行时间很早,至今还在流行。新的铜火熜金光闪闪,装进红、绿、白的生花生、桂圆、枣子等结婚“果子”,在钻有许多整齐小洞孔的盖子上,铺上一对双“囍”红字,显得又喜庆又贵重。铜火熜有大小轻重之别,但小型的极难看到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有一天在岩头陈市场边叫井头沿的地方,发现一位面有难色的老者,手掌上托着一只很小的铜火熜,轻声叫卖。这只长方形的小铜火熜长约13厘米,宽不到10厘米,高不过8厘米,遍体刻有花纹图案。与别的火熜不同的是它的铜鋬为双条,提起来时合二为一,放下时各向两侧落下,与火熜盖持平。工艺精细,小巧玲珑。十分吸引人们的眼球,大家都啧啧称好。有位老人说:“这种火熜是过去官家或财主人家的贵妇人和小姐用的,可以拢在衣袖里取暖,叫作手炉。”在场人只有看的不见买的。当时正是“三年困难”时期,虽然开价平平,物有所值。但谁会愿意饿着肚皮而出钱买这种只能看不能吃的“玩意儿”。至今近六十年了,我没有看到第二只这样精致的小铜火熜。 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出现一种全铁的火熜。它是用白铁皮圈成与篾火熜一般大小的圆圈,装铁皮圆底,再钉上双层窄铁皮弯成的火熜鋬就成产品。这种火熜轻便且不会跌破,一上市就成了抢手货。没几年,传统的篾火熜便逐渐淘汰。旧时,出现过一种篾、铁合成的火熜,用铁皮圈、铁皮底替代泥钵,形状为下半部垂直形,近口处突出加宽,但极稀少。 在使用火熜的过程中,曾出现两种实用的附带件:一是火熜盖。烘火熜容易烧破衣角衣边,“搁”脚不小心会陷在炭火上,鞋边鞋底也要烧焦。火熜盖量身定制,全用粗细铁丝编成而略大于火熜口的网式圆盖,盖上后可以完全避免被烧的现象。但使用的人不多,故不常见。二是小火锨(其形似锅铲而极小)。有时为调节火熜温度,就要拨灰拢炭火,有的人会就近找一段柴棒拨一拨,用完丢掉。也有人用手在火熜里挖几下,随手在衣裤上拍两记就了事。“仔细”的人在火熜鋬上用小链条挂上一把或铜或铁的小火锨,以便拨火灰,既方便又清洁。这种小火锨需要工匠打制,所以使用的人极少。有人会用细带(绳)吊一小竹片作拨火用,倒也方便可行。我曾经用一根稍细的铁丝弯曲成小火锨的模样,又用同样铁丝弯了几节小链条和一个适当的圆圈连接起来,挂在火熜鋬(pn)上,简单省料,实在实用,又不用请工匠加工。给家里每个火熜中都挂上一把,很方便。 火熜可供取暖,用处也多,但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隐患。有时不小心,会把衣角触到火熜里,直到有人喊:“谁‘破布臭’了?”意思是说衣服烧起来了,才发现烧了一个洞或布烧焦了。老人睡觉时用火熜烘被窝。严重的是人睡着了,忘记及时取出,而火熜倒在被窝里,轻则棉被烧破,重则皮肉受伤,甚至酿成火灾,危及生命财产的安全。这些现象,早年时曾听过见过,教训深刻。 笔者曾有一个与火熜相关的难忘故事 我清楚记得,九岁那年(年)冬天的一个晚上,大雪落了整整一夜。第二天很早去上学。漫山遍野的雪堆得厚厚的。雪还在飘,北风仍在吹。我背着母亲缝的布书包,除书外还放着一双稍好的布鞋,准备到校后换穿的。头戴一个大笠帽,脚上穿着破鞋,外包棕丝片,再用稻草裹住捆好。一手拎着火熜,上面盖着破瓦片,不让风吹走火灰。大清早,路上还没有人开过“雪路”。我一个人迎着风雪开道,向北一里半的圣云二校(即后来的礼张乡小学)赶路。当走上离校一百米的双溪桥上,一阵大风把大笠帽从头上吹下,盖住脸和前胸。我边走边戴正大笠帽。一不留神,脚踩到桥边,一晃滑下去,一只小手扳在桥石边沿,一只手拎着火熜不放。我知道,如果火熜倒掉或跌破,那今天肯定要挨冻。当时真是呼天不灵,呼地不应,多盼有人拉我一把!脸上泪水雪水混在一起往下流。扳住冰冷桥石的小手很快冻红了,开始感到有些麻木。最后还是坚持不住掉下溪滩。说也奇怪,人却稳稳地站住了,所幸的是手上火熜仍拎着。我想,或许是大笠帽起了“降落伞”似的作用。我只得小心地爬上溪岸,重新上桥,慢慢地移动麻木的双脚向学校走去。这件事刻在我的心上七十年了!只要下起雪,这件事就像电影镜头一样在眼前闪过,不由得泪眼汪汪。 火熜的旧事永在我的记忆中。 作者|石有才 编辑|赵哲越 审核|李少俊 原标题:《从前的冬天家家户户离不开它!》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dijincaoa.com/dmcgx/10590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以工代赈,赈活廉江乡村振兴源动力
- 下一篇文章: 人宠共居时代,年轻人的钱都花哪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