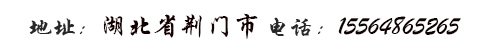跟爷爷上坟
|
每逢清明,我都会想起小时候跟爷爷去上坟的事儿。然而,那时候我们去上坟,并非一定在清明节这天,或早或晚,也或者刚刚凑巧。我没听见爷爷说起清明节几个字,那时也并不知道这个节日。在陇西老家,农历 月份,阳面的山上草儿已经开始萌动,抛开土,可以看见那细嫩的芽正从根部探出来,一点一点从去年的枯草中显露出浅浅的绿意。而阴面的山上,积雪尚未尽消,在天气晴朗的日子,就化出一些雪水,渗入梯田或者梗洼,山路也就跟着泥泞了起来。爷爷通常会择一个晴日,带我们去上坟。这是一个令人期待的日子。爷爷和父亲准备祭奠的一些用物,准备最多的是“铜钱”和“纸币”。父亲把一些麻纸折成书页大小,放在柳木砧板上,用铁凿子打成一串串的铜钱,每打出一沓,我们姐弟几个就一拥而上,七手八脚地把它一页一页分开来,然后装进一个麻袋子,直到一个麻袋快笼满才停止。爷爷在印板子上刷上红墨水,一张一张印着纸钱,面额都是一元。我现在想:现在的纸钱动辄就是一张一亿,那时候的人,为啥不把印板子上的数字写大一点,一张一百也行啊,至少印一张顶印一百张呢。可是那么多年,我们一直印着一元的纸钱,爷爷似乎从未动过其他任何念头,只是一语不发地一张又一张地,印上大半个时辰。奶奶和母亲在厨房忙活。奶奶蒸出暄软的馒头,再烙上一盆猪油盒子,母亲则是为我们做好早饭,再为先人准备献饭——那献饭通常是一大盘炒鸡蛋:母亲一碗打上十来个土鸡蛋,在大铁锅里倒上两勺胡麻油,“刺啦”一声,那香气瞬间就升腾了上来,直扑鼻。临出锅时再撒进去一把葱花,那香味越发别致了一些。这盘鸡蛋是给先人吃的,谁也不能提前吃,尝一口也不行。我们一边吃着碗里的面条,一边不时留意,看那鸡蛋出锅的时候,有没有个把不听话的,跳出锅,又刚好落在盘子外面,赫然立于锅台子上的,母亲是不会把它捡回盘子的,这样的鸡蛋吃了无罪。我们常常有这样的幸运,好像母亲常常手抖,尽管那时候她还很年轻。我家的坟在一个叫雪家沟的沟两边的山上,阴面和阳面都有。从我们庙儿社出来,顺着山脚的路右拐,就进了雪家沟。阳面山上的是祖坟,里面有我家太爷、太奶奶,还有三太爷、三太奶奶,应该有七八座的样子,二太爷呢?那么其他几座又是谁?我并不知晓。那时候太小,还不懂一一地问清楚,后来问过父亲,他似乎知道得也不是很巨细,现在,那些答案已经无从揭晓。二太爷和三太爷都没有留下儿子,二太爷连女儿也没有留下一个。祭奠他们的事儿全由爷爷一个人来做。阴面的山上,据说有两座坟,其中一个是爷爷的哥哥,他未成婚就英年早逝,另外一座,我记不清了,都因为一些乡俗,他们不能进祖坟安葬。阴面山上的路,在那个时候通常湿滑难走,进了沟里,我们就兵分两路,父亲独自去阴面山,爷爷带着我们姐弟去阳面山。我们的坟地在一块并不宽大的耕地的尽头,可是坟地的位置,却又四面延伸,倒是有了一大块较为宽阔的地方。四周的几棵大树繁枝若盖,应该是酸梨树,不像杨树那么笔直,也不像柳树那么柔软,当地人修房子、做家什通常都是用不上的,只有它的枝条,可以做连枷的骨子,用量有限,或因为此,它们才得以长成今天这个颇显茂盛的样子。到了坟地,在爷爷的指教下,我们开始从麻袋里拿出“铜钱”,一张分成两三条,分挂在所有我们够得着的树枝上,树上挂满后,我们再把它挂在灌木上,从坟堆边上,直到坟地的四周,不一会,就把铜钱挂满先人的院子。爷爷用镰刀割去坟堆旁过于杂乱的蒿草,这项工作比较耗时,还没完成一半,父亲已经从阴山上下来,跟我们会合了。父亲背起背篓,从一旁的田埂上背来土,一篓一篓地倒在每一个坟堆上,再用铁锨拍瓷实......我们姐弟几个早已忙完,就等着爷爷和父亲收工,那盘子里的鸡蛋应该已经凉透了吧。我们一边抓着土玩,一边朝地的那头张望:不远处,有一间房子,低低矮矮,门前是几尺宽的院子。那是一所村学,有四五个学生,只有一个老师。那个老师姓汪,他的脚先天残疾,朝内扭曲,走起路来一拐一拐,有些人就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“歪歪子”。虽是周末,汪老师一般都在学校,他没有媳妇,家里的房子也破败不堪,就住在学校。听说,这儿的学生冬天上学的时候,老师都把他们带在炕上上课,我满脑子的幻想,一时竟羡慕起他们来了。只是,汪老师始终没见出来过。终于,先人的院落看起来除了飘着的钱,一切都井然有序了,“房屋”也翻新得精神抖擞,爷爷收拾好镰刀,父亲放下了背篓,我们一起围坐在中间,等父亲从提篮里端出鸡蛋,拿出猪油盒和雪白的馒头......爷爷把猪油盒掰开,远远地抛向各处,父亲用筷子夹着鸡蛋,也同样抛向远处,我们的目光随着他们的手移动,抬起落下,落下又抬起,总怕父亲会不小心全撒了出去,又相信父亲不会如此大意。不出所料,在盘子里的鸡蛋还剩一半时,父亲停了下来,我们也终于松了一口气,可是耐心还得再延续一会。爷爷在坟前点了香蜡,把那些纸币和挂剩的铜钱点燃,再漩上一圈浆凉水,我们跪成三排,一起磕头。爷爷说,吃鸡蛋去吧!话音刚落,我们齐拥在盘子周围,一人一双筷子,不论谁先夹起, 口总是咽着唾沫先喂给爷爷,第二口喂给父亲。爷爷还跪在坟前,用一根树枝搅动着那些燃烧的纸钱,一边让它燃得更充分,一边又压着,不让风把火刮走。父亲开始打点地上的杂物,我们几个便爽快地吃了起来。那凉得发冰的鸡蛋,却比那家里刚出锅的更香,即便如此,我们也互相谦让, 一口总是推来让去,我给妹妹吃,妹妹给弟弟吃,有时弟弟又让给我。擦着油乎乎的嘴,我们跟着爷爷和父亲一起下山。回头,坟地里的满树的铜钱“呼啦啦”地飘着,再看一眼村学,汪老师还是没有出来。于是,我们便一溜烟跑下了山......山谷空荡,弟弟会大声地歌唱。爷爷奶奶在世时,上坟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儿呀!那时,年幼的我们未经别离,还不懂什么。爷爷去世后,上坟这件事,在我们的心里,变得完全不同。爷爷奶奶的坟地在新庄沟,爷爷去世已经整三十年了,可我在清明时节还未曾去看过他。也好,就让他一直记得我跟他上坟时的样子吧,那个他疼爱的孩子,在他的心里,一定要永世快乐的,不是吗?? ?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dijincaoa.com/dmcgx/9557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多多记日记萝藦
- 下一篇文章: 一中草木野草莓青春如梦